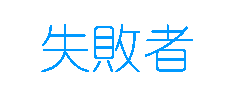蓮山的舊事
蓮山沒有蓮。山頂的神廟年久失修,院里一池碧水早已幹枯。
女人和女孩各自背著畫夾,行走在曲曲彎彎的小路上。晚霞燒灼著八月的黃昏,女孩紅撲撲的臉頰上滑下一滴汗珠,被她白皙的膚色襯得,紅得過了頭。女人則提了提肩上沈重的行李,里面鼓鼓囊囊,裝的是顏料罐子,正歡快地相互擠壓碰撞著。
她們是鄰鎮美術學校的師生。女老師花浮清約莫三十來歲,穿白襯衣,水磨藍的牛仔褲,齊肩的頭發染成棕色,紮馬尾。她的學生還是高中生模樣,長發白裙,裙擺隨步子搖動的時候,連夏風都好像清爽了起來。
她們在路旁等車。經過這個偏僻小站的只有一路公交車,是開往蓮山的。
幾乎就在一瞬間,她們剛放下畫夾和行李,再直起身子,旁邊就多了一位少女。
她有著一頭引人註目的火紅色短發,穿的卻是普通甚至有些破舊的亞麻布衣褲,兩手空空,也沒穿鞋。
穿白裙的女孩看她的第一眼,就感覺好像在哪里見過,但同樣又無端地覺得,那也一定是幾百年前的事情了。
不如說,雖然這個陌生女孩染著一頭時髦的紅發,但周身的氣質和所謂都市格格不入,仿佛她來自另一個時代。
尤其是那雙平靜的眼睛,不看她,但滿山晚霞打在她的眼角,只徒增一抹幽深。
「思存。」花浮清喊她,打斷了她的思索。
老師從隨身攜帶的背包里拆開一袋三明治遞給她,自己嘴里則嚼著餅幹。
久無人來的公交車站,石板地面的角落里爬滿了青苔。她慌忙轉身去接的時候,差點滑倒,被紅發女孩從身後一把扶住。
「……誒?謝謝。」
為了感謝這個素昧平生的人,白思存分了一半三明治給她,這才發現,她居然什麽行李都沒帶,一身輕得像一陣風。
「你也是來蓮山的嗎?」
紅發女孩輕輕嗯了一聲:「來旅遊。」
她的聲音比白思存的要低沈不少,卻並不讓人覺得沈悶,也許是因為她好看的頭發和眼睛。她和白思存站在一起,個子都差不多,身形也是十六七歲的少女。
少女和少女之間天然容易親近,白思存笑了笑,便和她攀談了起來。
「我們來寫生。」
紅發女孩緩緩擡頭,望了望雲遮霧繞的遠山:「蓮山已經,沒有蓮花了吧。」
這句話充滿了委屈和郁悶,她一說出口,卻只剩一縷輕飄飄的悵惘了。
「花老師說,我們只是來畫山景。蓮花什麽的,隨緣見吧。不過,老師倒是一直很擅長畫蓮花……」白思存說起她的老師的時候,特意看了看身邊女人的神情,她似乎並未註意到兩人,低頭在手機地圖上搜索著什麽。
女學生便又把目光轉回紅發女孩身上:「倒是你,什麽行李都沒有帶,山上荒涼,能行嗎?」
那人靜默了一會兒,說沒事,我知道在哪住。
她的下一句話就讓白思存摸不著頭腦了。
她說,蓮山曾經是我的家。
正當女學生思考著她是以前家住這里後來搬遷了還是別的什麽,花浮清指著手機喊她來看:「原來那座花神廟在山頂,從我們住的地方往上走,要兩個小時呢。」
白思存略有些不屑地勸她:「老師還是別惦記著那廟了吧。聽說,那里有時鬧鬼。」
紅發女孩插了句嘴:「不是鬼,是妖。」
她聽見陌生的聲音,下意識掃視了一眼那紅發女孩,目光卻也頓時定住了。
「你怎麽……」
她沒有繼續說下去。女孩和她對視的時候,一向平靜的臉色微微一變,仿佛雨前低飛的蜻蜓點起水面漣漪。
白思存不明所以地歪歪頭,「嗯?」了一聲,她倆這才如夢初醒,各自收回了目光。
紅衣女孩低頭的的時候,女學生竟然發現,她那悲傷的黑眼睛里,似乎有一簇紅火一閃而過。那火憤怒地燒起來,她卻面無表情,只略微皺了皺眉。
……那也是晚霞的原因嗎?
在去蓮山的車上,她曾問老師,第一眼看見她,是什麽感覺。
「很熟悉……」花浮清把頭疲憊地靠在座椅上。窗外的暮色漸漸暗下去了。
「她的頭發,眼睛,破舊的亞麻衣褲和赤著的腳。她站在那里,好像幾百年前就被遺棄過,而我,仿佛是那個把她落下的人。」
公交車呼嘯而來。紅發女孩卻沒有和她們一起走。鄰上車時,白思存向她喊:至少你告訴我們你的名字。
「紅蓮。」她以同樣的力度喊起來,微微前傾身子,「我叫紅蓮。」
花浮清和白思存訂的客房在半山腰。蓮山雖風景優美,然而地處荒僻,交通不便,即使是暑假,來旅遊的人亦不多。入夜之後,山上氣溫降了下來,便更顯冷清。
白思存從包里翻出一條薄毯裹在自己身上,推開門去院子里看老師。那人已支起了畫架,從她面前向下看去,滿眼是山腳村莊零落的燈火。她的畫布上卻只有幾痕濃青的遠山,山頂一座神廟的輪廓初見雛形。
她蘸了青色顏料的筆尖,正堪堪懸停在神廟屋頂上。
「花老師,怎麽一來就畫起這個?」白思存指了指她停筆的地方,輕輕問道。
花浮清出神地望著遠方,喃喃自語道:「廢棄了五百年的花神廟……怎麽會有燈光透出來?」
聽她這麽一說,白思存不由得打了個寒噤。
她想起了黃昏時那個名喚紅蓮的女孩,說山上有妖。但她怎麽會那麽清楚?
但是,害怕的勁兒過了,她想起那座據說已破敗不堪的神廟,心里不由得對紅蓮生出了同情。
「一個人住在那種高寒的地方……她會有多難過啊。」
狐貍是半夜來的。挑著個荷葉做成的燈籠,渾身白里透青。
紅蓮蜷縮在一堆破麻布里,不等他敲門,看見那燈籠光,便站起身把他迎進來。燈籠被擱在缺了一腿的木桌上,她用目光撫摸一下,眼里有些微懷念。
但開口問狐貍話的時候,聲音里又滿是淬了毒的仇恨了。
「水師傘都借來了嗎?」
「一切如你所願,紅蓮。」狐貍細聲細氣的,再配上那張美得有些詭異的尖臉,顯出森森鬼氣來。紅蓮卻並不怕。她恨了花神與白蓮多少年,和這狐貍就在一起廝混了多少年,他於她來說,只是助她完成復仇夙願的夥伴罷了。
五百年前紅蓮還只是紅蓮,和白蓮一起,生長在畫師的後院里。那畫師擅畫蓮,與之朝夕相伴,草木之身,靈智漸開。後來家中失火,畫師卻借此因緣飛升成花神,順手把白蓮也帶上了天宮,而那一刻紅蓮正被大火裹挾,花神誤以為那火是她放的,故而紅蓮後來反被天宮追殺。
後人就在花神曾居住的舊址上建了這廟。
因為差了畫師成神時的一握,紅蓮在大地之上,只能成妖。她介意的倒不是這身份之差,但是嫉妒白蓮可以日日伴花神身邊,享天宮清凈。此後日日躲避追殺,入妖界刻苦修煉,終於百年後闖入天宮,奪下兩人神魂欲滅之,卻不知為何,神魂從她手中滑落,不知所蹤。
鬼界偶然得了它們,因其已被紅蓮滅了神性,便當作普通的人魂,依照慣例,安排往生。
這兩位神由天上回人間,生生世世長久流連,忘了自己生前身,看紅蓮只是紅蓮。
她卻深悔自己當年失誤,又過了幾百年,查獲兩人現今為誰,這次發誓借神力徹底滅之,不願再出差錯。
「我尚需七天時間馴化水師傘,七天過後,暴雨洪水必將一應而至。」狐貍彎了彎尖嘴,輕快地跳上了破木桌,蓬松的白尾巴有一下沒一下地拂著紅蓮的赤腳,激得她趕緊往後縮,氣憤地伸出手打他的頭。
狐貍知趣地跳下來,落地的那刻幻化成人形,是個眼尾挑紅的風流鬼公子模樣。他換了一副嚴肅的樣子:「她們認出你來了嗎?」
紅蓮冷笑著說:「她們怕是把我忘得一幹二凈了。」
「是呀,畢竟是五百年前的事情……」
「她們忘了我,我可忘不了她們!」紅蓮暗暗握著拳,目光碰到桌角的那荷葉燈籠時,頓了一下,又接著自言自語,「七天!只消七天……你們就會把我當年的痛苦……通通體驗一遍!」
第一天,花浮清先帶著白思存在山上四處轉了轉。白天的蓮山脫去了濃重的夜色,顯出盛夏時的一片蔥綠來。她帶了昨夜沒畫完的第一幅畫,在山路上走來走去,卻怎麽也看不到那座破舊的花神廟了。
「老師,您在找什麽?」
「不信這里真的沒有蓮花。」
山間的生靈是多麽繁盛呀,車前草一直侵入了山路邊緣,野兔松鼠倏地一下從眼前躍過。山溪中浮萍飄蕩,可也只是一片碧綠,不見紅白。
白思存畫了好幾幅山景,可確實一枝蓮花的蹤影也沒有。花浮清則一直問:「沒有蓮花,何來的蓮山之名呢?」
「聽說,山頂的神廟還沒有廢棄的時候,院子里是有蓮花的。只是那里已經很多年無人去過了。」
說到這里,花浮清的腳步一頓,白思存也不禁縮住了口。她們都想起了昨夜山頂的燈光。
奇怪的是,當時她看得清楚,那燈似乎是青色,冷冷的,和山下人煙截然不同。
不知為何,白思存總覺得,花浮清對這座山上蓮花的追尋,並非單純因為她想畫它。
作為當地小有名氣的新晉畫家,花浮清擅畫各種花,其中最精妙的,當屬蓮花。白蓮氣質清越,紅蓮姿態淒烈,總能在她的筆下幻化出無限光彩。
而當一個星期前,她最得意的學生白思存問她,為什麽她們選擇來蓮山寫生時,她一開始顧左右而言之,直到臨行前的晚餐桌上,她開一罐啤酒,才對她說:「我不久前做過一個夢,夢里,我上了那花神廟,四周似乎有五彩斑斕的顏色,但我不記得那是些什麽花了。」
「莫非你是那廟主人?那你上一輩子就是花神了。」白思存打趣道。
花浮清不置可否。
她們都是親近藝術的人,她懂她是會為了一個看似無章的夢境而親身上山一趟的。
而自己於她亦徒亦女,當然願意陪她瘋一場。
況且,她自己也好奇,所謂花神廟里蓮花妖的故事,自己究竟是否有緣一見。
這一日,太陽落山時,紅蓮偷偷去看了她們。狐貍在她的身邊,兩妖都用了隱身術,向晚風聲大作,在專心作畫的花浮清和白思存兩人看來,他們存在的痕跡,不過是附近的草葉在不規律地搖動。
花浮清無意間向他們那邊看,手中的筆便改了畫法。她用手肘輕輕搗搗自己的學生:「你看,那邊的草的形狀,是不是和花瓣相像?」
流暢的弧線像未曾降落的流星一樣,劃過她的新畫布,留下青色的痕跡。
狐貍也有一雙妖的血紅的眼睛。他清楚地看見,紅蓮抖了一下身子,仿佛是被她的話惡心到了。但她的眼睛被風吹紅,雖然本來就是紅的,然而那不像太陽顏色,倒和蘸了夕陽的池水有幾分相似。
「第一夜。」
狐貍張開掌心,把縮小了的水師傘展示給紅蓮看。那凝著冰花滴著水珠的淺藍色的小傘,在他手里不安分地跳躍著,仿佛有生命一般。
「這玩意不愧是神物,難馴服得很。」狐貍小聲抱怨著,青色的妖氣從他周身散開,紅蓮怕人看見,趕忙抓了一把,如同捉一片雲霧。
「你呢?準備得怎麽樣了?」
「一整天忙著在山下布結界,好讓你六天以後充分發揮實力啊。」紅蓮沒好氣地回道。
狐貍看她兩手亂揮,好像怕極了自己妖氣泄露被人察覺,不由得嘖了一聲:「怕什麽,這荒郊僻嶺沒人會來,也沒人想偷窺你這蓬頭垢面破衣爛衫的樣子。」
他雖是揶揄的語氣,看向她的眼神卻溫柔卻略帶占有欲,那占有欲正因為求而不得而被壓抑得很好,再加上風流狐妖幾百年來早學會了一身翩翩公子氣質,乍一看倒以為他對她只有恭謹。
對此他們心知肚明。
兩人打鬧了一會兒,紅蓮卻突然收了笑容,伸出手指,「噓」了一聲。
他順著她指的地方望,半山腰有幾粒燈光。這不算稀奇事,那里有一家客棧,是花浮清和白思存下榻的地方。但看紅蓮的神情一直沒有放松下來,狐貍便半信半疑地張開雙手,結了個簡單的印,兩人的視野中,山頂到山腰的距離便一下子拉近了。
他有些驚異地註意到,穿白裙的女孩趴在窗欞上,正望著他們的方向出神。而那畫家女人在屋子里,背對著他們看不清楚臉,但她還在完善白天畫的畫,依據自己的想法,在畫布的邊角處憑空畫了一株紅蓮,又抹掉,又重畫,又抹掉,仿佛見不著實物,怎麽都畫不滿意。
「她……真在看我們?」
狐貍的聲音有些顫抖,「你不是說她認不出你的嗎?」
「別緊張。」紅蓮面無表情地說,「她現在是人,最多只能看見我們青色的燈光。」
「況且,」紅蓮遲疑了一下,「她的眼神……」
她說到這兒便停下了。她想狐貍大概也看到了,女孩的眼神里沒有任何恐懼或憤怒,清淩淩的,屬於人類的純黑的眼睛,盛著天真的好奇,以及真誠的關切。
隔著那麽遠,她當然知道她不是真的看到了自己。可是在狐貍結的印里,她們的距離一下子被拉近,仿佛那個已變成人類的女孩,此刻真的在和自己對視。
她莫名心生煩躁,啪的一下打落了狐貍還在結印的手。遠處的畫面如鏡片般裂開,露出夜晚黑漆漆的碎片。
「說起來,你為什麽還要我把這燈籠留著?」狐貍被她粗暴地對待了,倒也不生氣,慢悠悠地提起荷葉燈籠,準備離去,「明明你也知道,它只能發青色的光,像鬼火一樣。要是從不被人發現的角度,連這奇怪的光也不該出現吧?」
「別說了,就你話多。」紅蓮沈下臉來。
「什麽叫就我話多,你這也沒別人來啊。」狐貍真當自己能恃寵而驕了,還在一句一句補刀,直到被紅蓮拎著尾巴扔出窗外,隨後是那盞舊燈籠,可憐巴巴地滾落在他腳邊。
第二天,花浮清繼續慢慢向山上走,白思存覺得無聊,則下了一趟山。
蓮山上沒有蓮。但畢竟是七八月,山下的村莊倒有許多,她在那里買了兩袋蓮花糕。
畢竟暑假悠長,師生兩人的性子都像雲一樣,不拘形跡的。她不知道她們這次來山上寫生,會待多久,便想著買些點心,夜里也好填填肚子。
昨天晚上她睡得早,但是知道老師深夜都沒睡,一直在對著那幅畫冥思苦想。因為自己在睡意朦朧之中,總能感覺到她的響動。師生相伴多年,她不僅知道她在畫畫,還隱約明白她畫得並不順利。那股煩躁的氣息,像不再涼快的夏風,都快烘得她頭腦昏昏了。
今晚山頂上不知還有沒有青色的燈光啊……老師雖說想去花神廟看看,我看她也像近鄉情怯一樣,久久不動身呢……等等,什麽鄉,老師才不是神鬼,怎麽自己老是向這方面胡思亂想起來。
白思存在村中的集市穿行。她買完吃的,又撞入一間絲綢鋪,門口掛著鮮亮的布料。
她想起那個女孩,她破舊的麻布衣服,便在店內駐足,向女老板買了件紅裙。
「這衣服配紅顏色的頭發,好看嗎?」她有些忐忑地問她。
絲綢店的老板動作麻利,笑容溫暖而慈祥。她正把另一件綠色的裙子掛在高高的貨架上。那裙子像一片飄飛的荷葉。
「紅發紅裙,好看得很,你很會搭配啊,是藝術家嗎?」女老板沒回頭,但聲音很洪亮。
白思存被她的話惹得羞澀低頭,小聲回答說,「我只是一個畫畫的學生。」
躊躇半晌,她又指了指那個貨架:「那條綠裙子,也給我來一件。」
不知為何,感覺山下比她們住的地方要熱得多,也許是因為那里人太多了。
她擡起胳膊擦擦臉,抹了一手的汗。等回到山上的時候,正午的太陽已經高掛在頭頂。
回山上的路上她遇到了紅蓮。
不過是有過一面之緣的人,如果不是因為她那標誌性的紅頭發,簡直要認不出她就是那天那個和她們在公交車站上交談的人。但白思存還是認出來了,在即將擦身而過的時候,叫住她,把那件紅裙子送給了她。
「誒?」
這次輪到她疑惑了。
白思存有些手忙腳亂,她看看紅蓮,又指指自己:「我?我有的。」
她趕緊把手里提著的另一條綠裙子舉起來。雖然,這衣服本來是買來給花浮清的。
紅蓮沒再追問,但眼尖地瞅見了白思存手上另兩個袋子,上面印著蓮花的圖案,她知道那是從山下村子里買來的蓮花糕。
白思存感受到她的目光,剛要問問她是想嘗一塊嗎,卻聽見紅蓮有些鄙夷地哼了一聲,轉身跑開了。
但是還提著白思存送她的那件紅裙。
她跑得好快,身形又輕,像一枝柔韌的藤蔓,流水一般蜿蜒到山上去。
「第二夜。」
狐貍來的時候,紅蓮已經做好了蓮花糕,正把模具一個一個收進木盒里去。
她兩手沾滿面粉,沒工夫招呼狐貍,他便駕輕就熟地從窗戶跳進來,爪子剛伸向那糕,便又被紅蓮打落了。
「不是給你的。」
紅蓮探了探身,從桌子另一端取出兩塊新鮮的荷葉,把散落在桌上的那些精致糕點包起來。狐貍看得眼都直了,不滿地小聲叫起來:「合著我一整天忙著馴化水師傘,你在廟里只顧著浪費靈力讓紅蓮開花?」
「你居然把催開紅蓮當成浪費靈力……」紅蓮做出一份很是失望的樣子,「是誰以前天天嚷嚷我也想看一次蓮山的蓮花開呀?」
「你也沒給我看嘛。我來的時候後院的靈力早消散了。」狐貍很是不滿,席地而坐,揪住紅蓮的衣角打結,又解開,又打結。
他忽然失聲道:「紅蓮你的裙子怎麽了?」
狐貍是聰明的妖,一邊又聯想到紅蓮今天反常地做起了蓮花糕,便小心翼翼地猜測:「和山腰那位……嗎?」
紅蓮用沈默做了回答。
半晌,像是說服自己一般,她硬邦邦地說:「她們沒吃過好的,在山下買的雜牌貨,我看不慣。」
她的聲音變得陰惻惻的:「反正還有五天就要死了,讓她們做個飽死鬼。」
第三天。
花浮清想去山頂的花神廟,到了附近,又徘徊了很久。她在一處嶙峋的石壁前停了下來,石壁前是一小片枯萎的紫雲英。
為什麽想到這兒來?總不能單純因為那個夢。
思來想去,也許是因為,關於花神的那個傳說。
多年前同樣擅畫的人,攜一枝白蓮,在沖天火光里飄然飛升。可在後來的五百年間,人們說這里鬧鬼,鬼不常說話,周身萎頓黯淡,唯有一頭紅發如火焰般淒烈。
她想知道的是後來的事。
那個夢里,鬼面與蓮花形狀重合,吞噬了整個院落的火光里,瑟縮著的小小軀體,莫名讓人覺得委屈。
紅蓮從她面前的峭壁走過。花浮清的畫布上尚且一片空白。
她忽然叫住了她:「紅……」
她快三天沒見她了,已忘記了她的名字。
而紅蓮並未替她說下去,只是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,像是等待一個早就知道的答案。
花浮清心中的詫異轉瞬即逝。她見她換了樣子,紅發好好梳過,身上的裙子也是簇新的,看起來不再像初次見面時那個可憐的山野女孩了。
「你……就站在那里,側著頭,哎對,別動。」
她為她畫了一幅畫。畫她。
紅蓮覺得脖子酸酸的。她一直沒有動,仿佛還是有些害怕一般。強烈的陽光刺得她眼睛生疼,眸子里的那層紅光幾乎立刻要浮上來。天邊有金色的雨落下。她知道那雨人類看不見。那雨是狐貍用水師傘做的試驗。
和自己的仇人僅幾米之隔,紅蓮心中不知道是什麽滋味這里已經是很僻靜的地方,天光之下只有他們兩人,一站一坐,一靜一動。她的第一反應是不如就趁現在親手把她殺了,這對修行了五百年的妖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。但是她也知道凡妖殺不死人的魂魄,她所恨的人依然會一世世轉生流連於人間。而那不是她想要的斬草除根。
她站在那里微微出了神,眼前掠過無數並非幻影的記憶:院落,火光,青衣人驚惶的眼。燃燒著的橫梁落地時發出巨大的響動,呼喊聲徒然被蓋住。半空中出現的神跡。並未致命的一擊,但如同包裹著箭矢的雨水。萬古長夜……
但是現在。她想。她只是很好奇五百年後那個人畫出的畫是否和當年一樣。
「好了。」花浮清把筆插回畫具箱。
她看見水墨丹青變作了濃墨重彩,也許這種狂野艷烈的風格反倒更適合畫她。畫上是和五百年前迥然不同的風景,那人曾畫過無數遍的紅蓮變成了面前紅發紅裙的女子,依然能從身後的斷壁殘垣里依稀辨別出當年故居的影子,而偏院里空白一片。
蓮山沒有蓮。山頂的神廟年久失修,院里一池碧水早已幹枯。
「這簡直太奇怪了。」花浮清審視著自己的畫,像是對她,也對自己說道,「紅,你站在這里,好自然,就像你就像本就屬於這里一樣。」
她陷入思索,雙眼因而而顯得有些悲傷,「你是花神廟的主人嗎?」
「沒什麽好奇怪的。」紅蓮冷冷地打斷了她,「花神廟里本來就有蓮花,只是很久不開了而已。」
她心道,你曾經是花神。但是,這里不屬於任何人。
想到這里,恚恨之心蠢蠢欲動,仿佛又被五百年前的大火點燃。
但她最後只是略帶頹然地對花浮清說:「如果想畫蓮花,到我這兒來吧。蓮花會開的。」
她知道她也明白她說的「這兒」便是廢舊的花神廟。至於她想起了多少,或者說是否猜出了她們三人的隔世的往事,她不敢細想。怕她一眼看穿,也怕她一無所知。
她聽到的花浮清對她說的最後的話,是一句發自真心的贊揚。
「紅,你很美啊。」
「第三夜。」
紅蓮回到破廟,狐貍一來,就見她懊惱地拍著自己的腦袋,連連罵自己記性變差了:「怎麽就忘了給她送蓮花糕去了。」
「沒見到她?」
「見到了另一個人。」紅蓮接過狐貍手里的荷葉燈籠,「她給我畫了一幅畫。」
「怎麽說?」
狐貍跳上桌子,把身子靠在燈籠旁邊,支著腦袋,饒有興味地問她。
「只能說,技藝比起五百年前的花神,形不似神似啊。」
她回憶起白天那人嫻熟的運筆,卻每每在瞟自己一眼時,筆尖有略微無措的停頓。
但她必須承認,她已經有很久沒有看過這麽好的畫了。
也許一直以來,對她來說,畫得最好的,只有她一人而已。
「不管怎麽說該送的東西明天抓緊送出去吧。」狐貍懶洋洋地趴在她的腳邊。他身上很溫暖,即使是盛夏之夜,因為神廟坐落在清寒的山頂,她的光腳感受著他的體溫,也並不覺得煩。
「你是不是很累?」她關切地問道,「和我一樣,忙工作忙了一天吧?」
「雨師傘快要調試好了。過兩天我可能先試試讓它下一場大雨看看。」狐貍像是看穿了紅蓮的猶豫,目光銳利地盯著她,「你不會改變主意了吧?」
「怎麽可能。」紅蓮擲地有聲地向他保證,「為了這一天我謀劃了幾百年,不是為你,我也一定要去做。」
花浮清臉上不明所以的驚惶疑惑,白思存揚起臉時面對自己的清澈笑容,卻像古籍的書頁,在她眼前飛速翻過。
但新人載舊魂,初見一瞥,前後皆是萬古長夜。紅蓮有多少恨,終究淹沒了這薄薄的一頁。
第四天。紅蓮終於記得回送給白思存蓮花糕。
她淩晨時去,等太陽剛露出半邊臉,便飛速地回到了山頂,幾乎是用了逃一般的速度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在抗拒什麽。
花浮清伸手拉開了簾子。她醒得比她的學生早。
「這是什麽?思存,思存?送給你的東西嗎?」
白思存揉著惺忪睡眼,接過了老師手里的一盒糕點。
她還在說:「奇怪,附近的糕點店,都沒有這種包裝的……」
「啊……」白思存看見那盒子上熟悉的蓮紋,恍然大悟,「是我的一個朋友——」
「紅?」
「嗯。紅蓮。」
紅蓮送來的糕點當真是香甜綿密,與凡物不同。她們不知道這是來自妖界的手藝,只隱隱感受到那獨特的味道好像一個清涼的夢,夾雜著山風和雨水糾纏著的絲縷濕潤。
「她怎麽想起來給你送東西?」
「我送了她一條裙子……」
說到這里,白思存突然想起了什麽,放下剩下的蓮花糕就跑開了。她回來的時候,拿著另一條綠裙子。
「忘記送給你了。老師。」
「送我的嗎?」花浮清有些驚喜地接過。綠色的紗裙輕薄而光滑,在她的手中像一汪碧水一樣流瀉下來。
「只是感覺,莫名很適合你。」白思存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,「何況,和老師也認識十年了,就當是答謝……」
花浮清看著她那難得羞赧的樣子,忍不住輕輕笑了:「你很會選呢。想必那孩子,收到了你的禮物也會一樣開心的吧。」
「第四夜。」
狐貍今晚沒有留下很久。
雖然是夜晚,並不是月白風清的朗夜,天邊有濃重的陰雲,雨卻久久不來。
他把荷葉燈籠送來。朝著花神廟遠遠一拜,便又像一團雪白的火焰,消逝在茫茫山野之中。
他去忙著調試水師傘了。
紅蓮亦俯首,對著黑壓壓的夜色回禮。
回到花神廟來,一妖與一燈相對。她凝視著那盞古樸的燈籠,荷葉早已是枯黃的顏色,每隔幾十年,狐貍會在外面塗上了一層清漆,現在看來,倒顯得沈重。
她當然知道自己為什麽不願扔掉這舊燈籠。
她還記得當初狐貍把它送給自己的情景。那是花神的蓮池里最後一枝荷葉,難得沒有被大火摧毀。紅蓮那時候還是小妖,火勢蔓延差點波及了路過的狐貍,她憑借本能逃出院子,又拼死救了他,在她昏迷的那段時間里,狐貍待在她身邊,做了這盞燈籠。
對此,狐貍並沒有什麽解釋。他大多數時間里,是那副浪蕩公子樣,化為人形時,細長的手指敲叩著燈籠的竹骨:「看那被燒過的蓮池里,這幾片葉子孤零零的,怪可憐。反正咱們接下來還要趕路,照明工具必不可少,就順手做咯。」
的確。後來兩人竟總是在結伴趕路的途中。
狐貍成妖比紅蓮還要晚一些,初期得了她不少照拂。大概從那時開始,便暗暗決定要報恩。
紅蓮對此不很在意:「你們狐族好像總是有報恩情結,其實我的時間很多,慢慢修行也可,倒不一定需要你做什麽……」
狐貍卻只是垂下眼簾,說了句她當時還不太懂的話。
「我想幫你,不是為你,是為我自己。」
他陪她從小妖修煉成大妖,闖上天宮,又失魂落魄地回來,並不是因為失敗。他替她混入鬼界查輪回簿冊,耗時百年,得了個鬼公子的名聲。直到如今,紅蓮要借神力滅掉花神和白蓮五百年後的魂魄,但知道自己早已入了整個天宮的黑名單,也是他平靜地站出來,說,山中發洪水最合理了,我去幫你借水師傘。
他也並不是天天圍著她轉。有時趁夜色濃來看她,說幾番稀的家常話。白天照例遊山玩水,像每一只瀟灑的狐貍一樣。
她知道她是他眾多瀟灑中唯一的心執,卻沒有辦法回報什麽,只能以沈默維持這份心照不宣。
紅蓮想著過去的事情,一邊覺得這種懷念並不符合她的性子。但她仍然輕輕撫摸著那燈籠的邊緣,曾經粗糙硌手的地方都被歲月磨平了,若說不是懷念,便也找不到更貼切的詞語形容。
她對狐貍是沒有什麽心思的。那麽,對她們呢?
想到她們,總是很難繼續。紅蓮壓下心頭萬端思緒,嗖的一下竄出門。門外的山野之間,她隱了身,繼續建造復雜的結界,為三天後的殺戮做準備。她不想去想了,但身上那件紅裙卻讓她沒法不去想。它鮮艷得好像能壓住整個黑夜。
第五天,下大雨。
暴雨如註,傾盆而泄,地勢低處的芭蕉樹,雨水如斷線的珠子從葉緣顆顆滾落。稍小的灌木,皆被兇猛的雨打得彎下腰去。整個世界浸泡在綠色的、盛夏的潮水里。
紅蓮知道這是狐貍在試用雨師傘,不由得向天邊望了一眼。雨霧彌漫,她看不見,但心里明白,狐貍就在那雨水的開端,在雲與天的交界處揮扇,宛如如假包換的水神,一樣的白衣俊郎,唯有眼角一點挑紅,暴露他妖物的身份。
但她沒有想到她會在路上遇到花浮清和白思存。
女孩向她喊了一聲什麽,大雨迷蒙,她只能看見兩人似乎沒有帶傘,各自頭頂著芭蕉葉,在這樣突如其來的暴雨中,形同虛設。
白思存正奇怪著,紅蓮為什麽看起來不怕雨淋的樣子。
其實她並沒有使用什麽妖力,只是在這人間行走了五百年,已經不太在乎淋不淋到雨這種小事。
可對面是兩個人類。無論她們多少世前是什麽神什麽妖,這一世都是人類。
她招呼她們:「和我躲在一起吧。我知道哪兒有能遮雨的石壁……」
雨水依然沿著三人濕透的頭發流下。這里並不很高,盛夏天氣,好在雨天也不冷。
三人並排站著,相對無言,彼此都有些尷尬。奇怪,這似乎是第一次,紅蓮感受到自己還有尷尬的情緒。
她本以為,自己遠離人類的情感,已經很久了。
最後還是花浮清先打破了靜寂:「你做的蓮花糕很好吃。我和思存都很喜歡……」
「好吃得不像是屬於人間的東西。」白思存插嘴道,「紅蓮姐姐,你是神仙嗎?」
紅蓮心道,我怎麽就成了姐姐了……
妖物可保持不老容顏,然而她自認和白蓮是同樣年紀,是否因為自己畢竟過了幾百年,言行舉止中的滄桑之氣,已然藏不住了呢?
白思存剛一說完,她的老師就略帶嗔怪地說:「神仙有什麽好的,做東西好吃也不一定就不是人類的手藝,紅蓮也許只是哪家的姑娘,這糕點做這麽精致小巧,看起來倒像是送給心上人的……」
紅蓮不想再聽她們的混話了,抿了抿嘴,一言不發起來。
她們把一份人間煙火氣慷慨地送給她,而那慷慨是不自知的因為生生世世,三人早已走上不同的道路。紅蓮說不清此時自己是有些羨慕,還是嗤之以鼻,但她的心中絕不平靜。
她出了神,直到白思存輕輕敲她的腦袋。趕忙擡頭看她時,發現那人正眉眼彎彎地笑著。
花浮清在一旁替她說:「喊了好幾聲也不應,紅蓮,我說你啊,究竟是誰家的姑娘呢?」
紅蓮悄悄伸出手去,看起來像是承接從石壁邊沿滴下的雨水,但實際上她暗中施了個法術,她們面前的雨便停了,而放眼望遠方,該下的卻依然下著。
「這樣便可以走了。」花浮清眼前一亮,拍了拍手,招呼兩人抓緊這放晴的間隙趕路。
紅蓮又看了一眼,昏暗的天色隱隱開始發光。狐貍用水師傘做試驗,也快結束了。
「好神奇呀。」白思存依偎在紅蓮身邊,使她都不太敢動。
「太陽雨是這樣的。」紅蓮遮掩道,「東邊日出西邊雨嘛。」
她揚起臉看看她,目光里有欣羨。
「花老師,您是不是問我是哪家的姑娘?」
臨別的時候,她終於回答了剛才沒有回答的問題。
我是您的。她在心里這麽說。
花浮清她們聽到的卻只是,你們什麽時候來花神廟看一看呢。
紅蓮想,反正只有兩天了,告訴她們實情也無妨。
可是在這過去的將近一周里,其實隨時都有機會讓她對她們和盤托出的。反正她倆逃不開紅蓮專門為她們設下的結界,若還想讓她死,誰也沒辦法活。
但為什麽,她沒有說?
為什麽拖到現在,面對她們,萬般情緒湧上心頭?
她突然很想讓她們來花神廟看一看。一定要來。綁也要把她們綁來。
但還是希望她們能自己過來……過來看我。
狐貍說過的,你這里也沒有第二個人來拜訪過,不該怪這破廟淒涼。
一想起她們對那一世的往事還渾然不知……真是令人痛恨。
心痛,怨恨,好像都不是單純的憤怒的情緒。說起來,倒是更接近遺憾……
「第五夜。」
紅蓮突然對狐貍說,你是不是想再看看花。
狐貍啞然。
他想,她怎麽知道的?
「我比你早成妖幾天,讀心當然也比你有經驗。」她隨便應付著,扭頭走向後院。
淋了一天的雨,她的紅裙還沒有幹,袖子被挽到上臂,身形有些伶仃。
當初救下狐貍,自己力竭昏倒,現出的就是紅蓮的原型。其實她自己都不知道這有什麽好看的,但狐貍說,他最喜歡她這個樣子,親切,自然,令他想起繁盛的夏天。
可惜後來很久都沒有再看到了。紅蓮不是很願意以花形示人,於她而言,「蓮」這一字,容易讓她想起不願想起的事情。
所以狐貍聽到她這麽說,不由自主跟著她走向後院了。
他還沒踏出房門,紅蓮揚手帶起一陣妖風,「啪」的一聲把狐貍關在了里面。
狐貍委屈巴巴地蹲在門邊,欲言又止,最後只跟她說:「變好了喊叫我一聲哦,我要看。」
紅蓮沒應聲,但嘴角帶笑,像吹過繁盛夏天的一縷微風。她想,他還是老樣子。
她們也是。
她踏入了幹枯的蓮池。腳尖接觸池底碎石的那一刻,四周突然有清泉湧出。
狐貍推門而進的那一刻,看到的便是這副紅蓮搖曳的景象。
因為是妖物所化,紅蓮的周身帶著淡淡的金光。她無風自動,所有花瓣都像在顫抖,又像用力呼吸。
這紅蓮沒有葉子,每一桿花箭都筆直向上,指向天上的月輪。
他呆了呆,忽然心慌起來,跑過去想要摸摸她的莖幹,卻在快要觸碰到她時,害怕似的縮回了手。
「你要走嗎?」
「明天,白蓮邀我去做客。狐貍明晚不必來了,後天……」
「我知道怎麽做。」狐貍向她鞠了一躬。
他其實很想反駁什麽,但紅蓮一直沒有說話,他也就任由沈默充斥在他們周圍。
最後他又問了些什麽,但是依然沒有得到回答。
「你是為我開花的嗎?」
「還是因為……想要給她們看看?」
這一夜,紅蓮始終沒有變回人形。她就保持著在蓮池中搖曳生姿的樣子,伴著潺潺的流水聲,她嘆了口氣,叮囑狐貍:「後天洪水後,如果不能控製雨師傘,你自己趕緊往山下逃。」
雨師傘畢竟是神器,即使經過多日馴化,身為妖物的他,也只能暫時使用而已。
狐貍猛地擡頭,眼神灼灼,轉而變作清冷的淚光。
「我說過,狐族的傳統是報恩。」
紅蓮輕輕笑了,重復著說:「你們狐族的傳統嗎……」
不。狐貍在心中默默道。不是因為狐族。不是報恩。
第六天。
白天紅蓮在花浮清的客棧里做客,白思存從行李里拿出了一本相冊,里面記錄的大多是她與花浮清相處的點點滴滴。
「我父母在我很小時就去世了,花老師對我,亦師亦母。」
「什麽母,我看起來還沒有那麽老吧。」花浮清聽見了,笑著搗搗她,「最多算你姐姐。」
紅蓮也跟著一起笑了。
吃飯的時候,花浮清在廚房里忙活,白思存則先翻出兩袋三明治,扔一袋給紅蓮。
雖然是不同的款式,但這三明治還是讓紅蓮想起了當日她們三人在車站的初遇。
「別老是吃零食了,飯一會兒就好。」花浮清從廚房里探出頭來。
一時間,紅蓮覺得有些恍惚。
幾百年來,她一直以復仇為自己唯一的目標,現下所有的生活都是為了那一天的來臨,以至於她很少關註自己即時的情況。住的是從不修繕的破廟,不講究吃穿,常被狐貍嘲笑,那嘲笑中似乎也帶了一絲憐惜。
但此刻在花浮清和白思存這里,她居然第一次發現,原來現下的生活,也是可以並值得自己享受的。
「今晚就和我一起住吧。」
白思存附在她耳邊,輕輕地說。
我很喜歡你哦。她的眼睛分明這麽告訴她。
花浮清也過來,捋了捋她的頭發。
那感覺她忽然非常熟悉。
五百年前,花神還不是花神,她經常走在院落之中,思考著關於繪畫的各種事情。紅蓮記得很清楚,那時她便是這麽撫摸她伸出池外的花瓣,那雙柔軟的手輕輕捏捏瓣尖,就像在逗弄一只小貓的耳朵。
紅蓮像小貓一樣蜷縮起來了。
她們聊到很晚,包括花神的傳說。
她問她知不知道這些,兩人顯得都有點興奮,似乎這才是她們來蓮山的真正目的。
「我是在老師家的窗臺上發現那本怪談的。真的怪哦,作者出版社什麽都找不到,像是一本古籍。」
你當然找不到了。紅蓮心道,記載著往事的書,是我托狐貍趁夜里悄悄放在你家的呀。
「會覺得紅蓮可恨嗎?」
她這麽問的時候,心臟莫名漏跳了一拍。
「怎麽會。」這次是花浮清回答的,她聽到紅蓮兩字,皺了皺眉,後來又釋然了,似乎是作為現代人的她們不會真的相信那種巧合。
「如果紅蓮想殺花神她們,我覺得倒是合理……只是那麽多年,那孩子一定非常寂寞。」
紅蓮沒想過她居然會那麽回答。
花浮清說她寂寞,自己卻埋下頭,露出比寂寞更寂寞的神情。那神情紅蓮看得懂,比寂寞更寂寞的是被遺忘。
「她們沒有死哦。」紅蓮拍了拍她的手臂,像是在承認,又像是在安慰。
她閉上眼睛,腦海中回放起那一世的一幕幕:她手握著兩人的神魂,上面各附著一束藍色的火苗,她知道那是身為神族的神火,但那火是那樣灼熱,使她的手好像都沈甸甸的,好像每束神火都承載著一個人間。
她脫手,是因為她遠遠地看見了天階旁的蓮池。天宮里也有蓮池。不同於這里的水深火熱,遠離戰鬥現場的蓮池里,兩株蓮花依然紅紅白白地交錯著開放。
花神的神魂在她手里竭力躍動著,似乎要窮盡垂死前的最後一絲力氣,去親近那株離她最近的紅蓮。
而那景象,讓她的心跳也同現在這樣,紊亂了片刻。
說不清是不舍還是不甘,亦或只是單純的不小心,花神和白蓮的魂魄,從她的手里飛了出去。
她想起了自己的初心。即使那初心已被扭曲塗抹得面目全非。
窗外的月亮西斜了。五百年後的花神和白蓮,在紅蓮咫尺可探的地方,雙雙睡熟了。這是一個難得的晴夜。晴夜過後,這座山將醞釀遍野洪水。
前夜里聊到太晚,第七天,她們直到中午才起。起來也沒有什麽事,門前掛著花浮清前幾天畫的那幅畫,畫上的女孩紅衣紅發,栩栩動人。
她看著右下角的空白發呆。那里依稀可見許多塗改痕跡,花浮清試圖在那里畫些什麽花,但怎麽畫總覺得差了點什麽,便一直擱置了下來。
門的另一旁,地上散落著各種畫具。紅蓮撿起一支筆,試圖幫她補完這幅畫,但還是放棄了。
一來,她並不擅長這種事情,更何況已經過了幾百年,她大多數時間里避居山中,不通人事,很多畫具都叫不上名字了。
二來,她知道她為什麽畫不下去。
紅蓮漫無邊際地想著。
她的確是神。花神。老師。
五百年前她用神的力量催開整個春天,而現在,也依然如故。只是不再居於雲端,俯視這擁有諸多遺憾的人間。
創造的力量本來就是神遺落給眾人最後的神力,作為畫家的她,從來都不需要飛升。
她又一次凝視著花浮清的臉龐,直到她有些詫異地問她怎麽了。
那張臉,不施粉黛,然而成熟艷美,如她落筆一般,精純圓融,是輾轉了生生世世的生命。
窗外已經沒有雨了,但是天還陰著,一夜之間,剛被打掃好的門前臺階,迅速長出青苔,而紅蓮心中的某個地方,正在遠快於光陰地速朽。
大雨是在第七天淩晨落下的,正符合她和狐貍的預期。
雨水漫過木質窗欞,冰涼的觸感把師生兩人驚醒,驚心動魄的暴雨聲漫過耳膜。
幾乎是先於大腦行動,紅蓮把她們拉了出來,一腳踏入門口茫茫黑夜里去。
她終於決定了收回自己的復仇計劃。她的心中一直充滿了後悔,但又清楚地知道,五百年來,後悔的從來不是當初手握兩人神魂時,那恍惚的一瞬。
瘋狂地尋找她們,瘋狂地想要殺死她們,不過是想,再見一面。
可是已經見到了不是嗎?可是不需要以這樣的目的也可以見到不是嗎?
她還在想些什麽?
或許是因為,還沒有親口告訴她們。還不曾以真正的身份相認。
找不到狐貍了。但是紅蓮作為妖能感受到空中亂竄的神力,想必他被雨師傘牽製,也手忙腳亂得很。
她們不約而同迅速朝山上跑去。花浮清離開客棧之前,還不忘把自己的畫收拾帶走。雨水把她們拉起的手沖散了,有時又聚攏,像她們在山溪中看到的浮萍。遠處有令人震悚的轟隆聲響起,天地間,滾滾洪水正朝這無比渺小的三人湧來。
之前狐貍和紅蓮約好,洪水來後,不用管她們,待兩人淹死後紅蓮自去借神力滅魂魄,而狐貍負責把她從洪水中救走。
第五夜她又對他說,如果感覺神器難以控製,可自行離去。
她不願他這樣報恩的,即使那是他的情願。
這份愛對她來說到底是太沈重了。
任復仇蹉跎了自己的數百年時光,連身邊這份愛都未能好好端詳,也算是她眾多遺憾之一。
只是此生,也無法圓滿。
隔著渺渺茫茫的雨幕,紅蓮已經能看到,那一抹雪白的影子,泥水不沾,是狐貍從雲端向她奔來。
他化作了原形,跑得很快,如一道撕破黑夜的閃電。尖嘴銜著荷葉燈籠,燈光飄搖,明明滅滅。
「不是說你可以離開的嗎?」
尖利的風聲把她的話割斷了。狐貍長著一雙尖耳朵,此刻也只如山間遍生的草葉一樣,朝著風的方向生長,奔跑,再不停下。
他本來是要救紅蓮走的。他看她的目光如此熱切,任何人都不會忽視那其中焦灼的愛意。
可是她用力把身旁的另兩人攬到身邊,抱上了狐貍的背。
洪流吞沒了那瘦長的身子。這一夜紅蓮穿的不是破舊的麻布衣褲,而是那條鮮亮的紅裙,在昏沈沈的夜里,宛如一條翻飛的血河。
花浮清和白思存聽見了她最後說的話。漫天大雨也無法淹沒她竭力的叫喊——
「你是花神,你是白蓮,已經過去五百年了,但是傳說……是真的。」
「我不寂寞……我所追求的東西,早已經找到了。」
——只是我很久以來,都沒有發現而已。
等發現了,已經久到故人的面目都換了許多張。
但那又有什麽關系呢,我會在一次又一次的人生中,準確無誤地找到你。
花浮清終於看到了花神廟。
她一走進倒塌的院門,就覺得呼吸一滯。這里的確是和她有奇妙的宿緣。
狐貍化作人形,默默無語地凝望著院中的景象。蓮山沒有蓮。山頂的神廟年久失修,院里一池碧水早已幹枯。
然而,前天夜里紅蓮在這里留下的花,至今仍盛開著,惹得兩人一陣驚嘆。
但在同為妖族的狐貍看來,那不過是由紅蓮的妖術所幻化成的虛像,如山間看似停滯的雲霧,總有一天將會被長風吹散。
繪畫老師卻分辨不出這些,站在池邊看了許久,終於想起自己的畫,幸好被防水袋好好保存著,這一路奔波顛簸,竟也沒有損壞。
行李比剛上山時輕了不少,這是難免的事情。而花浮清提筆補完畫的最後一角時,恰好有山風吹起那紅蓮的花瓣,連帶著畫中人的裙擺似乎都在抖動,仿佛是她含笑和她打招呼一般。
她突然發現,這花神廟雖破舊不堪,滿天的風雨竟然無法撼動其半分。
白思存慢慢走出門去,她看不見那只白狐貍了,站在門口的只有一個風流俊俏的公子,仿佛是古書里走出來一般。
「我看過這本書。」她喃喃道。
狐貍好像沒聽見,依然頭頂一片荷葉,在看滿山暴雨翻滾。
荷葉燈籠在剛才與水師傘鬥智鬥勇時弄壞了。但是……
狐貍心想,也許紅蓮現在不會想要那個了。
畢竟在山上她對她們說的那兩句話,他也聽得一清二楚。
雨夜里沒有月亮,白裙子的女孩拍了拍狐貍的肩,狐貍轉過身去,她濕漉漉的眼睛好像在閃光,也落到了他的身上。
「你知道,紅蓮還會再回來嗎?」